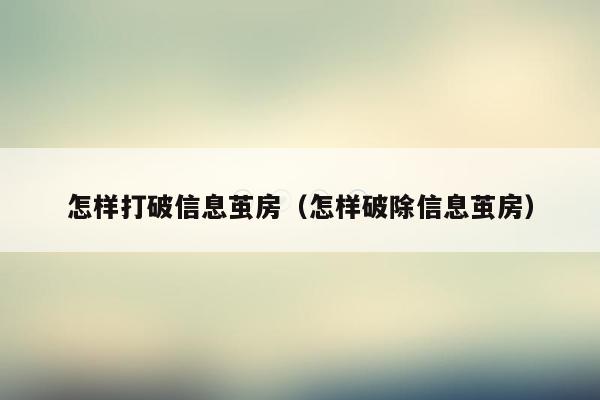本文目录一览:
关于信息茧房的文献综述
(一)关于信息茧房的理论研究
信息茧房 最早 由哈佛大学的桑坦斯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信息乌托邦》中提出,其认为信息茧房 是人们只听人们选择的东西和可以愉悦人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信息茧房是指人们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1]。
彭兰在《人人皆媒时代的困境与突围可能》中提及了“社交过滤网、圈子与信息茧房”,认为信息茧房与人的选择性心理有关,在传统媒体时代就存在,但是算法新闻、对信息过滤的社交网络以及具有圈层分化的社交平台在今天将其进行了放大[2]。
喻国明在《信息茧房“禁锢”了我们的双眼》中介绍了信息茧房的概念以及其可能产生群体极化和社会粘性丧失的负面效应,并认为应通过完善技术算法和个人媒介素养两方面改善方式;他的另外一篇文章 《个性化新闻推送对新闻业务链的重塑》,从新闻生产和受众两个层面分析了个性化新闻内容推送对新闻业的重塑,认为走出“茧房”效应应按照用户的社交数据和相关关系来“定义”潜在的需求[3-4]。
陈昌凤教授与她的学生一同撰写了两篇论文《权力迁移与人本精神:算法式新闻分发的技术伦理》、《信息个人化、信息偏向与技术型纠偏——新技术时代我们如何获取信息》,前者分析了算法式分发新闻的现状,认为新闻分发权由人移交到机器、新闻把关权后移、公民参与受到损害;后者说明了信息平衡对于社会和个人的重要性,介绍国外现阶段的技术性纠偏尝试:新闻应用程序“跨越分歧的阅读”、英国卫报“刺破你的泡泡”、华尔街日报“红推送、蓝推送”等[5-6]。
对于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蔡磊平在《凸显与遮蔽:个性化推荐算法下的信息茧房现象》认为个性化推荐系统提高了信息分发率、满足受众信息需求但也造成了信息茧房现象,令受众的全面发展和对现实社会认知判断产生影响[7]。同类的还有胡婉婷在《“信息茧房”对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破坏》中分析了信息茧房对公共领域建构的影响,认为其使得意见自由表达受阻、公众理性批判缺失、社会粘性削弱[8];苏颖在《传播的权力偏向》认为信息茧房与从众效应是产生群体极化的主要原因,在突发事件中,网民的负面观点和非理性情绪在“信息茧房”得到进一步强化[9];郭小平在《信息的协同过滤与网民的群体极化倾向》中通过对网络事件的讨论得出了信息超载后的过滤会带来群体极化的现象,并对民主和理性沟通带来威胁[10]。
对于信息茧房的解决策略,王刚在《“个人日报”模式下的“信息茧房”效应反思》中认为个性化信息服务强化了“信息茧房”效应,扩大了知识鸿沟,媒体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提供高质量新闻内容[11];刘华栋在《社交媒体“信息茧房”的隐忧与对策》中分析了信息茧房的成因,发现社交媒体、个人议程设置、协同过滤算法三者为茧房效应的形成提供条件,提出了构建多元化信息接收渠道、构建人行道模式、提升媒介素养的建议[12]。
(二)有关信息茧房与具体案例的结合研究
部分研究多从具体案例的特点出发,结合信息茧房的相关概念特征进行质性分析。如杨慧的《微博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描述了信息茧房在微博中的体现并针对微博提出了相应改进策略[13]。许志源、唐维庸在《2016美国大选所透射的“过滤气泡”现象与启示》中以2016年的美国大选为研究事件,发现入们的“准感官统计”在新媒体时代受到技术算法的干扰,呼吁媒介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负起社会责任[14]。
在能够搜集到的国内定量方面研究中,李佳音在《基于个性化推荐系统新闻客户端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中选取今日头条作为个性化推荐系统的代表,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调查今日头条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信息茧房效应的影响[15];彭晓晓在《信息时代下的认知茧房》中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选取的微博样本用户进行编码、界定、挖掘,并结合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分析,以此验证“茧房”效应的存在性问题[16]。两者对于本研究都有很好的启发性,但前者选取今日头条,后者通过一个范围很小的“微博上广告业界与学界的意见领袖”群体来推定信息茧房的存在,在样本范围以及差异性上有些不妥。
(三)总结
通过对文献进行整理,发现现有关于信息茧房研究都是基于桑坦斯教授的理论,侧重于对于信息茧房的理论再认识,并且都停留于行为模式的简单陈述。部分研究结合了具体案例,但是仍是泛泛而谈地去佐证桑坦斯教授的理论和观点,没有对信息茧房现象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缺乏对于观众行为和信息平台的深入讨论研究。
(四)参考文献
[if !supportLists][1] [endif]李清池.通向信息乌托邦的道路——读《信息乌托邦》[J].中国法律,2010(02):19-20+73.
[if !supportLists][2] [endif]彭兰.人人皆媒时代的困境与突围可能[J].新闻与写作,2017(11):64-68.
[if !supportLists][3] [endif]喻国明.“信息茧房”禁锢了我们的双眼[J].领导科学,2016(36):20.
[if !supportLists][4] [endif]喻国明,侯伟鹏,程雪梅.个性化新闻推送对新闻业务链的重塑[J].新闻记者,2017(03):9-13.
[if !supportLists][5] [endif]陈昌凤,霍婕.权力迁移与人本精神:算法式新闻分发的技术伦理[J].新闻与写作,2018(01):63-66.
[if !supportLists][6] [endif]陈昌凤,张心蔚.信息个人化、信息偏向与技术性纠偏——新技术时代我们如何获取信息[J].新闻与写作,2017(08):42-45.
[if !supportLists][7] [endif]蔡磊平.凸显与遮蔽:个性化推荐算法下的信息茧房现象[J].东南传播,2017(07):12-13.
[if !supportLists][8] [endif]胡婉婷.“信息茧房”对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破坏[J].青年记者,2016(15):26-27.
[if !supportLists][9] [endif]苏颖. 传播的权力偏向[D].中国政法大学,2011.
[if !supportLists][10] [endif]郭小平.信息的“协同过滤”与网民的“群体极化”倾向[J].东南传播,2006(12):43-44.
[if !supportLists][11] [endif]王刚.“个人日报”模式下的“信息茧房”效应反思[J].青年记者,2017(29):18-19.
[if !supportLists][12] [endif]刘华栋.社交媒体“信息茧房”的隐忧与对策[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04):54-57.
[if !supportLists][13] [endif]杨慧. 微博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4.
[if !supportLists][14] [endif]许志源,唐维庸.2016美国大选所透射的“过滤气泡”现象与启示[J].传媒,2017(16):54-56.
[if !supportLists][15] [endif]李佳音. 基于个性化推荐系统新闻客户端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7.
[if !supportLists][16] [endif]孙亮.信息时代下的“认知茧房”[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04):52.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很努力,才能跳出“信息茧房”的怪圈
作者:隽君
这是一首灵巧别致的诗歌,相信不少人都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它。
我依稀还记得,在过去的岁月里,在少年时期信息不那么发达的情境中,内心那种平静又微微泛起波澜的感觉,生活节奏慢,却又在平淡之中蕴藏着某种不可名状的趣味。
曾几何时, 我手写书信,粘上邮票,投入到信箱里,寄给另一个学校的朋友,总怀着期待的心情不厌其烦地翻看有无对方的来信,我们就这样如此来往,倾诉衷肠。
曾几何时, 我总是要拿着MP3到书店录入歌曲,每录入100首歌,收5块钱。那时候很少人有电脑,只有书店有那种比较厚又笨重的台式电脑,能够导入歌曲。
曾几何时, 我第一次拿着手机,和同学初次上网聊天,按键打字出句子总是慢的,却只能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待着彼此的回复。最尴尬的是,还能被对方发现自己同时跟几个人对话,显示为对方繁忙、正在输入的状态。若聊天对象是稍有好感的男同学,总免不了尴尬,有些许罪恶感。如果打字回复太慢,会让对方心里不高兴的,所以我只能当从不会、不懂,训练自己的打字速度了。我们互相窥探彼此QQ空间发布的说说和照片,还有腾讯微博,虽然大家发表的蛮多都是偏向于二次元、非主流和流行语录,但也忍不住上前点赞,连评论都是深思熟虑、小心翼翼放上去的。那时候连会使用百度进行搜索,都是一件让同学夸奖、值得别人欣赏的事情,可以拿来标榜自己不是常人认知的书呆子,为人灵活变通、有趣,颇又有一种“学习又好、思想又潮、又懂得应用生活、技能点多”的优越感。
曾几何时, 我开始用上了触屏更加灵敏的手机,那种手触的方便和新鲜感让我感到小雀跃,我可以通过这个和他人高效率联系了。读书时期我们都建立了自己的群,然后在群里上传照片。看着拍摄的照片,依旧保存至今,有着过往的回忆,心里是欣喜万分的。
曾几何时,我开始有了人生中第一台电脑,屏幕很大,可以下载大量的应用软件,可以存储各种文件,整个页面让人感到豁然开朗——那无疑是步入新世界的大门。仿佛在电脑的另一端,有着永无止境的、值得我们 探索 的东西,神秘、危险、又迷人。
紧接着步入了大学,急匆匆地考了计算机考试,节奏很快,老师、学校给的信息狂轰滥炸。
从那时起,我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彻底地掉进了信息大爆炸的漩涡 ——但当时我们称这是知识的海洋,直觉和过往的经历告诉我们,这绝对是有利而无大害的。
因为还深刻记得小学时候学的一篇文章——《渴望读书的大眼睛》,获得教育的机会已经如此难得,我们又怎能说它的不是?如果有不好的地方,那一定是我们自身的错。我们偏执地这么认为,这种偏执,也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鲜明特征,多多少少有点网瘾而不自知。
带着对知识的敬畏,我们开始在信息的海洋里漫无目的地 探索 。
我们已然分不清楚什么是 信息和知识 ,也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信息和知识,就连老师都告诉我们应试教育里学的东西仿佛就是知识,他们说知识能够改变命运。
我们开始被“信息茧房”困扰着。
可是很多人开始变得 浮躁 ,而且 社会 风气也变得如此 ,甚至把浮躁当做习以为常,把浮躁视为骄傲,把浮躁当成现代人的常态。因为很多人都如此,“从众心理”让我们忘了反省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潜意识告诉我们,只要和身边大部分人一样,我们就不会有危险。
但是这是错的。
去掉浮躁 ,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一直以来都应该成为一种像吃喝拉撒一样的习惯而已,就像每天刷牙一样的好习惯。不必搞得惊天地泣鬼神,因为去掉浮躁,仅仅是拥抱最好的自己而做出的第一步而已。
去掉浮躁 ,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这是一件值得高度重视的事情。一个人,如果连这个都无法做到,那么他也就这么慢慢废掉了,只等着时间来制裁。
去掉浮躁 ,这也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应该成为一个人骨子里的修养和底蕴,这个是不能拿出来炫耀、彰显品位的。它可能不能帮助一个人一定能够成事,但是却是成事的基础,是高楼大厦的地基。
正如泰戈尔《纸船》这首诗中描写的心境,那正是我们需要找回来的状态。
深呼吸3秒,去想象,静静地去体味这首诗吧,这首诗蕴藏着怎样的心情呢?对成长的渴望,对远方的憧憬,对交流的渴望,对神秘事物的向往,对爱和美的感悟。朴素而单纯,内心平和、喜悦、怀着希望,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心境啊。
……1……
……2……
……3……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也是我们要回归的。我们应该做一个纯粹的人。在这个灰度的世界,能够一生把自己活得如此干净纯粹,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能力。
你听说过“信息茧房”一词吗?
“信息茧房”是什么? 有人说它存在,有人说它不存在。有人说这个概念是虚的,有人说它确实存在 ,就像电磁场一样。关于它到底是虚的,还是实在的,人们各有各的观点和意见。
这种现在,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性格和行为,对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思维境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通过潜意识或者获得的信息限制着人们在生活中的种种决策,使得 社会 之中不同人群之中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平等,造成了群体极端想法的产生,威胁着 社会 的和谐和稳定发展。
除此之外,哪怕在信息传输较快的今天,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也不意味着不同的地域、地区就趋向于信息平等了。比如一线城市就和三四线城市甚至农村,居住的人知道的事物都差不多一样,在今天这依旧是不可能的。
昨日人民网发表《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一文中末尾写道:
“随着我国青少年触网年龄的不断降低,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已是当务之急。《法治 社会 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就指出,加强全 社会 网络法治和网络素养教育,制定网络素养教育指南;加强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引导青少年理性上网。只要政府与学校、家庭与 社会 团体携起手来,就一定能让青少年在面对网络信息的海洋时明辨是非, 健康 成长。”
不止是青少年,这也同样适用于成年人,中老年人,适用于一切活到老学到老的人,适用于所有还没有放弃自己的人。
让我们也努力吧,跳出信息茧房的怪圈!
怎样避免活在信息茧房之中?
信息茧房的本质是共鸣(或共情)成瘾。企图用认知提升,或者专业的学习是无法打破成瘾性的,就像一个认知再高、专业技能再强的人,一旦沦入毒瘾或性瘾,也很难戒掉。从心理舒适度出发,人们会倾向相信那些,自己的经历、教育、社会身份、情绪回路、创伤、易构建情景等等可以共鸣的东西,而无论其是否真的有道理。
而且,人们会倾向于相信,在心理暗示上带有褒义词汇,且与自身超我匹配的描述,哪怕这个描述本身换一种说法,就是明显的悖论。由于对自己视野或认知以外的盲区缺乏基本的系统性概念,人们还会倾向于相信,用自己的经历或周边的环境结构去解释盲区的规律和结构。
这些不仅仅是心理舒适度的需求,它们还带来(融入主流群体的)安全感、(识别敌我边界的)清晰感、(自己很优秀的心理暗示带来的)社会成就感,从而生成了大量的多巴胺反馈。这就导致,人们在选择信息和分析信息时,会围绕感性共鸣(或共情)来进行定义和筛选,将无法获得多巴胺的部分认定为假(或无价值的、邪恶的、不道德的、需要被消灭的),从而隔离了自洽圈和舒适圈以外的信息。
同时,自洽和舒适感所带来的大量多巴胺,会阻止人们用理性和方法论去推测,表面信息背后的逻辑,以及隐藏的拼图,会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用熟悉范式(而不是理性推导)去进行认知定性。综上所述,戒除共鸣(或共情)成瘾,是避免活在信息茧房中的唯一路径。一些相对简单的训练方法:
1,学会解析信息及其包含的逻辑的底层,通过对信息的极简化处理,去掉形容词和各种诱发情绪的褒义词,把底层逻辑暴露出来,从而在规避共鸣(或共情)的情况下进行真伪和程度性的检查。
2,使用合订本模式,有意识的跟踪曾经对自己产生巨大共鸣,或巨大情绪刺激的信息,在热点消退和自己的情绪消退后,进行分析、复盘,寻找当时自己的共鸣点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认知偏差,以及思考如何在未来规避这种偏差。
3,有意识的寻找你认可的信息或观点的对立面,并分析其合理性的程度。
4,反向代入:即不仅仅代入你条件反射的立场和角色,也代入与之对立的角色。
5,极化推断:即将信息及其逻辑,向极端化方向推演,看是否出现明显谬误,如果有这个明显谬误,再反推当前信息及其逻辑的适用范围或真伪。
以上,本文无意贬低认知提升的重要性,但在信息茧房层面,认知提升的效用非常有限,感性的认知被自洽包装成论理的辩证的认知,这种习惯非常常见,离开以上的这些训练模式,所谓的认知提升,其实很可能是自己看到更多信息数量(而非质量)之后的臆想。